第三届·21世纪保险圆桌论坛
主持人:唐学鹏(本报资深编辑)
嘉宾:
郝演苏(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主任)
鲍勃·吉布森(恒安标准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
齐莱平(中美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董事总经理)
董宏良(首创安泰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
袁通君(恒安标准人寿保险公司市场部总经理)
谢忠(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赖军(招商信诺人寿保险公司副总经理)
本报记者 赵萍 北京报道
【编者按】
保险业是中国金融业第一个实现全面开放的行业。
1992年,美国友邦保险公司获得了中国对外资保险开放的第一张牌照,自此,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大幕徐徐拉开。
入世成为外资保险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契机。截至目前,外资保险公司已在1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立机构和开展业务。
五年河东,五年河西。从当年的产品、服务、营销创新,到如今的经营管理和人才战略探索,外资保险仍不遗余力拓荒,虽然业内挖角、高管频繁更替仍不时困扰着他们。
外资保险究竟给中国市场带来了什么,又有哪些亟待完善之处?21世纪第三届“保险圆桌”特邀外资保险高管和专家共同探讨“入世五周年——外资保险在中国”。
首创安泰的60个合规政策
《21世纪》:入世五年来,外资保险公司为中国市场带来的是单纯的资本存量的增加,还是大量创造性的资源,如人才、技术、经验的传递?
郝演苏(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主任):在中国的整个金融市场中,保险市场是外资进来最多的,无论是独资、合资的数量都大大超过银行业。官方研究结果显示,外资(保险)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是6%左右,但如果把外资在中资保险公司中参股的部分都计算在内,将超过34%。
入世前夕大家讲“狼来了”,现在来看到底狼来没来?我感觉外资对中国保险业产生了压力,但这个压力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严重。
谢忠(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是朋友来了。这是我国保险业开放的必然趋势,对老百姓是好事,对于保险经营者来说,经营技术层面,产品和营销模式、战略等方面有很多很好的借鉴。
齐莱平(中美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董事总经理):外资能带进来什么?是钱、人才,还是技术?我想是新的理念和技术,通过引入外资激活刺激整个行业,让行业加速发展。主体增加后,销售渠道的增多,老百姓的选择也就多了。
董宏良(首创安泰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没错,外资带来的绝不是单纯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整个市场的竞争,在营销模式和人才战略等方面的示范效应也是有的。
总的来讲,前一阶段我们注重外资的营销模式,后阶段是外资的风险管控模式。我刚到任时,看到公司有六十几个合规政策,有点抗拒。但外方认为如果这60个合规政策都不能实施,公司就会死掉,由此可见外资在风险管控上所起的作用。
袁通君(恒安标准人寿保险公司市场部总经理):对于合规性问题,刚开始时的确有些反感,觉得他们就是公司里的警察,但真正到了这种文化能够深入人心的时候,员工就会认为这是一家负责任的企业,更注重于长期经营,员工会更有信心。
《21世纪》:产品、营销、精算,尤其是在合规管理上,外资的示范效应显著,他们与中资公司还有哪些差异?
鲍勃·吉布森(恒安标准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我们非常注重产品创新、精算、财务管理的技能以及客户服务。接下来是通过人才的本地经营,形成合资公司的文化,以及合资公司的战略。
袁通君:很多国外公司经营重点放在投资方面,销售环节的利润空间比较小。但在中国市场上,由于投资的限制,很大的利润空间来自于销售环节。西方国家对销售环节监管得非常严格,而我们是在产品上监管得比较严格,所以中西方有很大不同。
赖军(招商信诺人寿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大部分中资企业还是想越大越好,认为市场占有率有了以后就能赚钱,其实不一定,很多外资企业经验告诉我们,不一定越大越赚钱。还有一个人才问题,不一定有外资参与才能管理人才,像平安,同样可以直接引入外籍管理人才。
应对“挖角”
郝演苏:我的学生作过一次调研,发现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和中资一样,也是上来先挖人,所以他们认为外资公司和中资公司的策略相同。这个结论各位是否认同?
齐莱平:大家都是高估了市场,低估了竞争。你非常注重打造产品、渠道、人才培养等等,但市场不规范,一些其他的公司复制和挖角的成本,远比自创成本少得多。现在(外资公司)是44家,五年以后可能变成88家,如果这种事情继续下去,结果变成整个市场在内耗,最后受益者就是跳槽的人,业务品质没提升,就是薪水提升了。为此我们多次跟监管层沟通,看新产品、新渠道是不是可以有保护期,同时对市场秩序也应该有所保护。
《21世纪》:可不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保护机制?海外的经验怎样?
齐莱平:我没有见过在全世界任何的国家和地区有对销售模式的特别保护,而对新产品的保护有很多,保护期六个月或一年不等。但我刚谈的是普遍的挖角行为,上世纪90年代末、2000年初的香港我也看到过这样的现象,整个行业新契约保费增长十几个百分点,可总保费是减少的,后来我才明白,这是(由于)一帮人从A公司跳到B公司,把旧保单全部卖掉,在新公司重新上一份,最后吃亏的是老百姓。
所以,我认为在开放过程中,监管机构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定出一些游戏规则,例如严格限制每个公司同业增员的比例。
鲍勃·吉布森:齐总所说我在英国十年到十五年前也看到过,在英国处理这样的问题方法就是通过监管机构,对销售流程进行强制监管,要求销售人员必须从客户利益出发,全面了解客户的理财需求,为客户提供理财建议,而不是单独销售产品。
《21世纪》:旧保单卖掉换新保单会损失客户利益吗?
鲍勃·吉布森:其实没有明确的答案说好还是坏。从客户价值角度上看,客户把保单转移到新公司,营销员从中获得双倍的佣金,客户的价值也相应受到损失。但如果新公司产品的投资回报高于保单转换中产生的损失,对客户来讲就是好的事情,如果反过来就是不好的事情。
《21世纪》:除了监管机构制定行业规范外,公司自身有没有好的办法克服“挖角”问题?
董宏良:我觉得很多问题出在销售管理上。为什么外资公司比较重视绩效?因为(公司)要确定是不是选对代理人。要稳定营销团队,首先要看代理人是否能够挣到钱,只有赚到足够的钱,他才愿意参加营销团队,通过这个机制去获得他应有的报酬。
鲍勃·吉布森:我们相信通过职员制这种营销模式,我们对营销队伍会有更好的管控,销售品质会更高,销售团队的留存率也会更好。显然,采用这种模式在初期要比代理人的模式成本高,提供基本的底薪,会给业务带来一定风险,所以公司内部更多的工作是为营销员提供更好的培训,更加积极的活动量管理,以及更好的激励方案,这样他们才能为公司带来更大的价值。
赖军:如果创新是很简单的,就很容易被模仿,如果独特,又有一套完善的系统支持,就不容易被模仿。我们专注地做我们认为的强项,例如电话或银行的直销,就不怕模仿。不过,我们看到的很多不是模仿,不是通过提高自身的技术含量后去竞争,而是简单粗糙的竞争,减价、挖角、加工资。
人才本土化之途
《21世纪》:中高层“水土不服”是人才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问题是否有新的解决思路?
郝演苏:一定要发挥本地人才的功能。在北京、上海有一家寿险公司一直排在最后一位,而集团内的另一家财险公司却非常成功,北京分公司开业一个月的保费就超过了寿险公司一年的保费。后来我发现,财险公司主要的业务都来自本国客户,而寿险公司部门下面很多小机构的管理人员也都来自本国,很难和中国民众接触。所以本土化的问题,是外资寿险公司要更多考虑的一个问题。
齐莱平:我也发现,二十几家合资外资公司里,所有由母公司派来的老总,没有一个是本土出生、本土长大的。这个可以理解,因为需要和总部充分的沟通,但全国大概120多个分公司的老总里,居然真正的本土人才大概不到两成。这个我认为就讲不过去了,分公司老总一定要很贴近市场,要用本土化人才。
《21世纪》:既然有本土化需求,各位对未来的人才战略有何打算?
齐莱平:我们公司的三大战略:多元化行销、区域化、本土化。我认为,本土化是能够决定中美大都会最终发展成什么样公司的最重要的一环,其他战略都可以变,如果这个公司没有足够的本土化人才的聚集,没有共同理想往前走的话,这个公司没有前途。
赖军: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的策略因为渠道的关系比较特殊,主要靠自己培养本土的人才。除了日常培训,经验分享外,我们每年还有一个很正规的人才评价体系,对每个人的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再用这个体系给他做培训计划和发展计划。此外,针对每一个重要的岗位,我们还有专门的人才培养计划。
鲍勃·吉布森:我们采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理念,就是充分利用每个人的一技之长,使他们在工作中感到愉悦和满意。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了解他们的长处,为他们的一技之长找到适应他们的岗位,并提供一个公平的工资支付平台。
袁通君:作为恒安标准的老员工,我有一个亲身的体会,公司对人才的吸引力来自几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薪酬的吸引,一个是文化的吸引,另一个是管理能力的吸引。高层的管理能力决定你最终发展的前景。
董宏良:外资公司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国际化,给个人的发展空间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市场。以我们首创安泰来讲,大概一年有20个人在香港培训,也有到其他亚洲地区的,培训并不是短期的,他要在那边实干,持续了解整个ING产品发展的规范及做法,了解合规的流程和整个系统的架构。




 公司简介
公司简介 品牌故事
品牌故事 新闻动态
新闻动态 荣誉责任
荣誉责任 全媒体阵营
全媒体阵营
 寿险|意外
寿险|意外 养老保障
养老保障 健康保障
健康保障 财富管理
财富管理 少儿保险
少儿保险
 服务指南
服务指南 自助查询
自助查询 消费者权益保护
消费者权益保护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年度信息
年度信息 重大信息
重大信息 专项信息
专项信息 其他信息披露
其他信息披露

 “值得信赖的家庭保险专家”
“值得信赖的家庭保险专家” “轻松便捷更快一步”
“轻松便捷更快一步” “美好生活抖起来”
“美好生活抖起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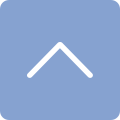











 公网安备12010102000280号
公网安备12010102000280号